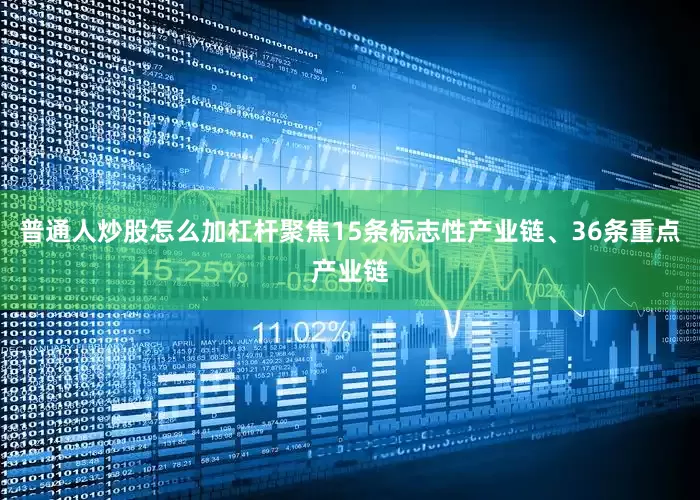01
1934年10月的一个深夜,瑞金城外的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里,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。陈赓正在批阅最后一批学员的毕业报告,突然,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。
“报告!”一个浑身湿透的通信员站在门口,雨水顺着他的军帽檐滴落在地板上,在昏黄的灯光下形成一小滩水渍。
“进来。”陈赓抬起头,看到通信员手中紧紧攥着一个油纸包裹的信封,上面印着中革军委的火漆印。
通信员双手将信封递过来:“首长,中革军委紧急命令,要求立即送达,立即执行。”
陈赓接过信封,撕开火漆印,展开里面的文件。他的眉头渐渐皱起,目光在那几行字上反复扫过。文件的内容很简短,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他心上:
“鉴于当前形势,中革军委决定:一、立即恢复红军学校建制;二、组建军委直属干部团;三、任命陈赓同志为干部团团长,宋任穷同志为政委;四、限三日内完成组建,随时准备执行特殊任务。”
文件的最后,是几个熟悉的签名。陈赓知道,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到来。
他走到窗前,透过雨幕望向远方。广昌战役的惨败还历历在目,5500多名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。现在,中央苏区的地盘一天天缩小,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。所有人都明白,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移即将开始,但没人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
“通信员,”陈赓转过身,“立即通知宋任穷同志,半小时后在这里碰头。另外,通知肖劲光、韦国清、林芳英、罗贵波、余泽鸿等同志,明天早上六点,在学校大礼堂开会。”
通信员敬了个礼,转身消失在雨夜中。
陈赓重新坐回桌前,开始在纸上列出一个又一个名字。这些名字,每一个都代表着红军中的精英。他知道,中革军委要他组建的,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,而是一支能够在最危急时刻扭转乾坤的精锐力量。
半小时后,宋任穷推门而入,身上还带着雨水的寒意。这位刚从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委任上调来的年轻指挥员,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“老陈,什么事这么急?”
陈赓将文件递给他: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宋任穷快速浏览了一遍,抬起头:“干部团?这是要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起来啊。”
“不仅如此,”陈赓站起身,在屋内踱步,“你注意到‘特殊任务’这四个字了吗?我判断,这支部队很可能要承担保卫中央的重任。”
宋任穷点点头:“广昌失守后,形势确实危急。听说敌人已经调集了100万大军,准备对苏区进行最后的围剿。”
“所以,我们必须在三天内,组建起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。”陈赓的声音里透着坚定,“这支部队的每一个战士,都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。”
02
第二天清晨,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,聚集了近百名军政干部。这些人中,有刚从前线下来的团长、师长,有在红军大学深造的高级指挥员,还有各个特种兵科的技术骨干。
陈赓站在台上,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肖劲光坐在第一排,这位曾两次赴苏联学习、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革命,眼神沉稳如水。旁边的韦国清,虽然年轻,但已经是红军大学的总支书记,未来的路还很长。
“同志们,”陈赓开口了,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,“我知道大家都很疑惑,为什么突然把你们召集起来。现在,我可以告诉你们,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支特殊的部队——军委干部团。”
台下一阵窃窃私语。干部团?这是个什么编制?
陈赓继续说道:“这支部队将直属中革军委领导,编制虽然只有团级,但它的任务和性质,远超过一个普通的团。简单地说,这将是红军的‘御林军’,是在最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精锐部队。”
肖劲光站了起来:“陈团长,这支部队的具体编制是怎样的?”

“一个上级干部队,四个步兵营。”陈赓回答,“上干队由红军大学的优秀学员组成,主要是营团级军政干部。一营、二营从第一、第二步兵学校抽调连排长级别的干部。三营是政治营,由政治科的指导员和干事组成。四营是特科营,包括炮兵、工程兵、机枪等技术兵种的骨干。”
林芳英举手发言:“团长,我们这些人,很多都是从师长、团长的位置上下来的,现在去当营长、连长,会不会…”
“会不会觉得委屈?”陈赓接过话头,“同志们,我陈赓从红军学校校长变成干部团团长,宋任穷同志从师政委变成团政委,我们觉得委屈吗?不!因为这支部队的使命,比任何职务都重要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声音变得更加低沉:“实话告诉大家,中央苏区已经守不住了。我们即将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移,而这次转移能否成功,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这支部队的表现。”
会场里陷入了沉默。每个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余泽鸿,这位曾任上海党中央秘书长、建宁独立师师长的老革命,缓缓站起身:“陈团长,既然使命如此重大,我愿意到干部团来,哪怕当个普通战士都行。”
“我也愿意!”韦国清站了起来。
“算我一个!”罗贵波也站了起来。
很快,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。看着这些红军的精英,陈赓的眼眶有些湿润。他知道,这支部队已经有了灵魂。
接下来的三天,是疯狂的三天。各个部队的精英被迅速抽调,编入干部团。这些人中,有身经百战的老兵,有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,有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军事理论家,还有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。
最让陈赓感到欣慰的是,这支只有1000多人的部队,几乎每个人都掌握着一门或多门军事技能。上干队的学员,个个都能指挥一个营甚至一个团作战。四营的特科人员,精通各种技术兵器的使用和维修。就连负责后勤的人员,也都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好手。
10月10日,干部团正式成立。这一天,瑞金城外的训练场上,1000多名精英战士列队站立。陈赓站在队伍前面,看着这支崭新的部队,心中既有豪情,也有隐忧。他知道,未来的路充满了凶险,但他相信,这支部队一定能够创造奇迹。
03
1935年1月28日,贵州土城。
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,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。陈赓趴在山头的战壕里,用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动静。在他身后,干部团的1000多名战士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。
“团长,侦察员回来了!”参谋长跑过来报告。
一个浑身是血的侦察员被两个战士架着走过来,他的左臂已经被子弹打穿,鲜血染红了整条胳膊。
“团长…敌人…敌人不是两个团…”侦察员喘着粗气,“是郭勋祺的两个师!还有后续部队正在赶来!”
陈赓的心一沉。原本情报说敌人只有两个团,现在变成了两个师,兵力相差了六倍!而此时,红军主力正在按照原定计划展开,如果不能及时调整,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立即向军委报告!”陈赓果断下令,然后转向干部团的营长们,“各营注意,准备迎击敌人主力!记住,我们的任务是挡住敌人,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争取时间!”
很快,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,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成群的敌军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,向干部团的阵地扑来。
“稳住!都给我稳住!”陈赓在战壕里来回奔走,“记住你们都是干部,是红军的骨干!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!”
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着仅有的几门迫击炮,准确地轰击着敌人的冲锋队形。炮弹在敌群中爆炸,掀起阵阵血雨。但敌人仗着人多,一波接一波地冲上来。
“一营,左翼有敌人包抄,立即派一个连堵住缺口!”
“三营,组织政工干部到一线,稳定军心!”
“二营,准备反冲锋,把突入阵地的敌人打出去!”
陈赓的命令一个接一个,整个干部团就像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,虽然人数不多,但战斗力惊人。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,每一个干部都能独立指挥作战。
激战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敌人发起了十几次冲锋,都被干部团打了回去。阵地前沿堆满了敌人的尸体,鲜血把雪地染成了红色。

就在这时,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: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已经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,正在紧急调整部署,命令干部团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,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。
“同志们!”陈赓站在战壕里大声喊道,“中央相信我们,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!我们绝不能让中央失望!”
“绝不让中央失望!”战士们齐声呐喊,士气大振。
太阳渐渐西斜,敌人的攻势却更加猛烈了。郭勋祺亲自来到前线督战,把他的王牌部队都投入了战斗。
就在最危急的时刻,肖劲光带领上干队的预备队冲了上来。这些营团级干部组成的预备队,战斗力更是惊人。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指挥,自动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,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。
“陈团长,左翼敌人被打退了!”
“右翼阵地巩固了!”
“正面敌人开始撤退!”
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传来。郭勋祺没想到,他的两个精锐师,竟然被红军一个团挡住了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,这个团的战斗力如此顽强,打法如此灵活,简直不像一个团,倒像是一个军。
夜幕降临时,敌人终于停止了进攻。陈赓巡视着阵地,看着那些疲惫但眼神依然坚定的战士们,心中充满了自豪。这一仗,干部团伤亡了200多人,但他们挡住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,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更重要的是,这一仗打出了干部团的威名。从此,“陈赓的干部团”成了敌人闻之色变的部队。
04
1935年2月25日深夜,遵义城外的一座破庙里,陈赓正在和几个营长研究地图。煤油灯的光芒在地图上跳跃,照亮了每一个人紧张的面孔。
“老鸦山,这是关键。”陈赓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高地,“谁控制了老鸦山,谁就控制了遵义。现在吴奇伟的两个师正在向这里集结,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占领这个制高点。”
就在这时,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一个满脸血污的传令兵冲进庙里:“陈团长!紧急情况!张宗逊的部队在老鸦山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反击,张宗逊负重伤,钟伟剑团参谋长阵亡!阵地即将失守!”
庙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老鸦山一旦失守,不仅遵义保不住,红军的整个战略部署都将被打乱。
陈赓霍然站起:“还有多长时间?”
“最多两个小时!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!”
陈赓扫了一眼地图,又看了看表,果断下令:“全团立即出发!告诉同志们,我们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赶到老鸦山!”
“一个半小时?”林芳英吃了一惊,“团长,那可是三十多里山路啊!”
“就是爬也要爬过去!”陈赓的声音斩钉截铁,“通知全团,轻装前进,除了武器弹药,其他东西全部扔掉!”
凌晨两点,干部团开始了一场生死时速的急行军。山路崎岖,夜色如墨,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着。有人摔倒了,爬起来继续跑;有人的鞋子跑掉了,光着脚也不停步。
陈赓跑在队伍的最前面,他知道,每一分钟都关系着战局的成败。在他身后,是1000多名红军精英,他们中的很多人,都曾指挥过大规模的战斗,现在却像普通士兵一样,拼尽全力地奔跑着。
山路越来越陡,很多人已经跑不动了,开始手脚并用地爬行。宋任穷一边爬一边鼓励着战士们:“同志们,再坚持一下!老鸦山上的同志们在流血,在等着我们!”
凌晨三点半,当干部团终于看到老鸦山的轮廓时,山上的枪声已经稀疏了很多。显然,守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
“上刺刀!”陈赓拔出手枪,“跟我冲!”
没有任何战前动员,没有任何作战部署,1000多名精疲力竭的干部团战士,就这样发起了冲锋。他们的喊杀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响起,如同惊雷一般。

正在进攻的敌军完全没有想到,红军的援军会来得这么快。更让他们惊恐的是,这支援军的战斗力如此凶悍,每一个战士都像是不要命的猛虎。
肖劲光带领上干队从左翼迂回,韦国清指挥四营的特科兵从右翼包抄,林芳英和罗贵波率领三营从正面突击。这种默契的配合,根本不需要任何指挥,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指挥员,都知道该怎么打。
吴奇伟的部队开始混乱了。他们原本以为胜利在望,却突然遭到如此猛烈的反击。更可怕的是,红一军团的主力也开始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。
“撤退!快撤退!”吴奇伟意识到大势已去,急忙下令撤退。
但为时已晚。陈赓的干部团像一把尖刀,深深地插入了敌军的心脏。溃败很快变成了溃逃,吴奇伟的两个师丢下大量的武器装备,狼狈逃窜。
太阳升起时,老鸦山上飘扬起了红旗。陈赓站在山顶,俯瞰着遵义城,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一仗,干部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但他也清楚地看到,很多战士已经累得直不起腰,有的人脚上全是血泡,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了。
宋任穷走过来,递给他一个水壶:“老陈,你说得对,这支部队确实是红军的‘御林军’。”
陈赓接过水壶,喝了一口,苦笑道:“御林军?我看更像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。”
“疯子好啊,”宋任穷也笑了,“敌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这种疯子。”
05
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月,红军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。在这场被毛泽东称为“得意之笔”的战役中,干部团始终伴随在中央纵队左右,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。
有一次,毛泽东亲自来到干部团视察。他看着这些精神饱满的战士们,对陈赓说:“陈赓同志,你这个团可不简单啊,个个都是宝贝。”
陈赓回答:“主席,这些同志确实都是红军的骨干。他们中很多人都可以独立指挥一个团,甚至一个师作战。”
毛泽东点点头,意味深长地说:“正因为如此,我才把他们放在身边。危急时刻,这支部队就是定海神针。”
事实证明,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,干部团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他们时而是先锋,为大部队开路;时而是后卫,掩护主力撤退;时而是预备队,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。
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太平渡。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渡过赤水河,但敌人的追兵突然出现,威胁到渡口的安全。陈赓带领干部团迅速占领渡口两侧的高地,构筑防线。
敌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,想要夺回渡口,切断红军的退路。干部团以一当十,死死地守住阵地。战斗最激烈的时候,陈赓亲自端起机枪扫射,宋任穷带头发起反冲锋。
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,干部团伤亡过半,但他们守住了渡口,保证了红军主力的安全。战后,毛泽东特地来到干部团,握着陈赓满是血污的手说:“陈赓同志,干部团立了大功!”
06
1935年5月,金沙江畔。
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,干部团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1000多人减少到不足800人。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却丝毫没有减弱,反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变得更加强悍。
这天深夜,陈赓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:抢渡金沙江。
“金沙江水流湍急,两岸都是悬崖峭壁,”陈赓在简陋的指挥所里对各营长说,“敌人已经控制了主要渡口,我们必须另辟蹊径。”
韦国清提议:“我们可以派小部队化装成敌军,骗取渡船。”
肖劲光摇头:“太冒险了,一旦被识破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,一个当地向导被带了进来。这是一个瘦小的彝族老人,他告诉陈赓,在下游二十里的地方,有一个隐秘的渡口,只有当地人才知道。
“但那里水流更急,”老人说,“而且只有两条破船,很危险。”
陈赓当机立断:“就从那里渡!韦国清,你带四营的工兵先去,把船修好。肖劲光,你带上干队负责警戒。其余各营,做好渡江准备。”

第二天凌晨,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,干部团开始渡江。两条小船在汹涌的江水中摇摆不定,每一次横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。
陈赓站在江边,看着战士们一批一批地渡过对岸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突然,一条船在江心被激流冲翻,十几个战士落入水中。
“快!救人!”陈赓大喊。
会游泳的战士纷纷跳入江中,拼命地营救落水的同志。经过惊心动魄的抢救,大部分人被救了上来,但还是有三个战士被汹涌的江水卷走,永远地留在了金沙江。
渡江持续了整整两天。当最后一批战士登上对岸时,敌人的追兵才姗姗来迟。他们看着滔滔江水,只能望江兴叹。
站在金沙江北岸,陈赓回望来路,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支干部团,从组建到现在,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,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,证明了自己是红军真正的精锐。
07
1935年6月,四川安顺场。
大渡河就在眼前,这条被称为“天险”的河流,水流湍急,波涛汹涌。对岸,敌人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,机枪阵地密布,任何试图强渡的部队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
陈赓站在河边,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敌情。在他身边,干部团的主要军官都聚集在一起,商讨着渡河方案。
“情况很不妙,”肖劲光放下望远镜,“敌人不仅控制了所有渡口,还把能找到的船只都烧毁了。现在我们手里只有一条小木船。”
“一条船?”林芳英苦笑,“这要渡到什么时候?”
就在这时,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:石达开当年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。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,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“历史不会重演!”陈赓斩钉截铁地说,“石达开失败了,但我们不会!干部团,准备强渡!”
宋任穷担忧地说:“老陈,用一条船强渡,代价会很大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用最精锐的力量,打开一个缺口。”陈赓转向各营长,“挑选最勇敢、最有经验的战士,组成突击队。记住,这不仅是一场战斗,更是一场和历史的较量!”
5月25日拂晓,强渡开始了。
第一批17名勇士登上了那条摇摇晃晃的小木船。他们都是干部团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,有的是神枪手,有的是爆破专家,有的是格斗高手。领头的是二营的一个连长,叫孙继先,这个山东汉子以勇猛著称。
“同志们,”孙继先在船上对战士们说,“咱们干部团的脸面,就看这一次了!”
小船在汹涌的河水中艰难前行。对岸的敌人发现了他们,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打来,在船边激起无数水花。一个战士中弹倒下,鲜血染红了船板,但没有人退缩。
就在小船即将靠岸的时候,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,巨大的水柱差点把船掀翻。孙继先大吼一声:“快!冲上去!”
17名勇士跳下船,冒着弹雨向敌人的阵地冲去。他们的身影在硝烟中若隐若现,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。经过惨烈的肉搏战,他们终于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滩头阵地。
“成功了!”陈赓激动地挥舞着拳头,“快,第二批,第三批,立即出发!”
但渡河的速度太慢了,一条小船一次只能运十几个人。眼看着对岸的敌人援军越来越多,滩头阵地岌岌可危。
关键时刻,韦国清带着四营的工兵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他们在上游找到了几根粗大的木头,连夜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木筏。虽然简陋,但能够一次运送三十多人。
随着援军源源不断地渡河,滩头阵地逐渐稳固。陈赓亲自带领干部团主力渡河,与先遣部队会合。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,他们终于彻底击溃了守军,控制了渡口。
战斗结束后,陈赓站在大渡河畔,看着那条立下奇功的小木船,感慨万千。他对身边的宋任穷说:“你看,我们做到了石达开没能做到的事。”
宋任穷点点头:“是啊,历史没有重演。但代价……”

他没有说完,因为两人都知道,这次强渡,干部团又失去了几十名优秀的战士。这些人,每一个都是红军的宝贵财富,都有着成为高级指挥员的潜质。
08
长征路上,干部团创造的奇迹远不止这些。在飞越泸定桥的战斗中,他们配合红四团,用血肉之躯在铁索上开辟通道;在翻越夹金山时,他们不仅自己全员通过,还帮助其他部队运送伤员和物资;在草地行军中,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顽强的意志,成为部队的标杆。
更重要的是,干部团在长征途中还承担着培养干部的重任。每到一地宿营,陈赓都会组织学习和训练。他常说:“我们不仅要打胜仗,还要为红军培养更多的指挥员。”
事实证明,这种做法是有远见的。长征途中,由于战斗减员,很多部队都急需补充干部。干部团就像一个流动的军校,源源不断地向各部队输送合格的指挥员。据不完全统计,长征期间,干部团向各部队输送了300多名连排级干部,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红军的中坚力量。
1935年10月,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,干部团只剩下不到500人。但这500人,个个都是百炼成钢的精英。他们不仅经历了长征的全部战斗,还在最危急的时刻一次次力挽狂澜。
在吴起镇,毛泽东专门接见了陈赓和干部团的主要干部。他握着陈赓的手说:“陈赓同志,干部团是长征的功臣啊!没有你们,很多关键的战斗都打不赢。”
陈赓谦虚地说:“主席过奖了,这都是大家的功劳。”
毛泽东摇摇头:“不,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知道吗?蒋介石的将领们都在研究,为什么红军能够突破重围,完成长征。他们不明白的是,我们有你们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。”
确实,在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中,多次提到了这支神秘的“红军精锐”。他们不明白,为什么每次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,总会冒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,把他们的计划打乱。
多年以后,当年的敌军将领郭勋祺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红军有一支部队,人数不多,但战斗力极强。每次出现都在关键时刻,每次都能扭转战局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陈赓的干部团,号称红军的‘御林军’。”
09
长征胜利后,干部团并没有解散,而是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干部团的很多成员都成为了八路军、新四军的骨干。陈赓出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,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。宋任穷、肖劲光、韦国清等人也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将领。
新中国成立后,这些从干部团走出来的将领们,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55年授衔时,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,肖劲光同样是大将,韦国清、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。据统计,从干部团走出的开国将军多达30多位,其他军师级干部更是数以百计。
但更多的干部团战士,永远地留在了长征路上。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,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天,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,永远镌刻在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上。
1960年,陈赓在病床上口述回忆录时,专门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干部团的故事。他说:“干部团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传奇。这支部队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,但它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,是无法估量的。可以说,没有干部团,就没有长征的胜利。”
他特别提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:“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红军战士,每一个人都有着光明的前途。但为了革命的胜利,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。我常常想,如果他们活着,新中国会有多少优秀的将领和建设者啊。”
1961年3月16日,陈赓在上海病逝。临终前,他还在念叨着干部团的往事。他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说,陈赓最后说的话是:“告诉活着的老战友们,干部团的精神不能丢……”
时光荏苒,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,但干部团的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。这支只存在了一年多的部队,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,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。
他们是红军的精锐,是长征的脊梁,是永远的“御林军”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,在最艰难的时刻,总有一群人愿意挺身而出,用自己的牺牲换取胜利的曙光。这就是干部团的精神,这就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。
今天,当我们走在和平的阳光下,不应该忘记那些在黑暗中为我们点燃火炬的人。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模糊,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陈赓日记》(1934-1936年),解放军出版社《红军长征史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《红军干部团战史》,军事科学出版社丁秋生:《长征中的干部团》,载《党史文汇》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》,解放军出版社
泰禾优配-广州炒股配资公司排名-线上开户的证券公司-股票配资开户费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知识网可以把脓血和脓根拔出来
- 下一篇:没有了